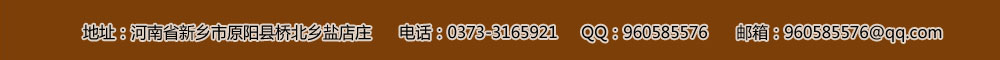罕见病国家目录前瞻从地方罕见病名录看
罕见病领域步入,值国际罕见病日设立十周年之际,大家企盼的最重磅消息该是什么?毋庸置疑,是“罕见病国家目录”有望出台。
伴随着年的部分喜讯,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。去年第12届国际罕见病与孤儿药大会暨第6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上,权威人士透露,“官方定义的首批罕见病目录也正在研讨中,包含多病种,届时相关罕见病的药品进口审批和医保支付或都将因此受益。”
我们常说,罕见病在中国缺乏官方定义,以目前国内现状而言,为罕见病下定义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;与此同时,罕见病群体大多处在被忽视的状态,罕见病又大都需要终身维持治疗,相关药物往往价格极其昂贵,绕开这个“坑”,出台罕见病目录是明智之举。
实际上,虽然罕见病国家目录尚未问世,从各地方到医学界,已经有了多个版本的罕见病目录。
早在年,青岛就发布了《关于建立城镇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(试行)》。本意见首开先河,第一次明确将罕见病纳入大病医疗保障体系中,实现了罕见病医疗保障制度的从无到有。截至年上半年,纳入门诊大病保障的罕见病种达到20种。
浙江则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医保基金结余和罕见病发病诊治等情况,经组织专家论证,把罕见病医疗保障病种范围暂定为戈谢氏病、渐冻症、苯丙酮尿症。这三种病的特点是能够诊断,有药可治愈或控制、缓解。
年,广东也发布了本省罕见病目录,其遴选也是依据发病率相对较高、诊疗方案明确的原则,共收录46种罕见疾病。
年2月,上海发布《上海市主要罕见病名录(年版)》,纳入内分泌与代谢、肾脏、免疫、血液、消化、骨骼心血管、五官等系统罕见病计56种,用于本市开展罕见病宣传、筛查、诊断、治疗、康复和进一步制定罕见病防治的相关政策参考。
年12月,医院学会罕见病分会在京成立,同时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罕见病研究项目。该项目总目标是在未来4年建立统一标准的国家罕见病注册登记系统(NRDRS),其中,首批入选的罕见病共59种,分为4大类,包括:心肺肾罕见病、内分泌代谢与血液系统罕见病、神经骨骼与皮肤罕见病和儿童罕见病。
年2月,中国国内首本以临床实例为主的罕见病专著《可治性罕见病》问世。该书由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联合国内各个领域的相关专家编写,分为上下两篇,共收录了种可明确诊断、有治疗方案的罕见疾病,涵盖内分泌与代谢、血液、呼吸、免疫、肾脏及风湿、心血管等多个专业。
年3月,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成立了6个相关学组,分别是罕见病儿童肾脏病学组、罕见病风湿免疫学组、罕见病神经病学学组、罕见病儿童神经肌肉病学组、罕见病心脏病学组、罕见病临床评价药学组。
不难看出,罕见病目录是为罕见病药物审批、医保政策服务的,而罕见病的“可治性”,是筛选病种是否收入目录的重要参考标准。
问题来了,在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目录中,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才符合“可治性”的标准呢?
这关系到未来收入国家目录、现在依然神秘的“多病种”到底是哪些疾病。说来,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,也蛮有趣的:目前已发现的疾病中,能够通过药物或医疗手段完全根治(健康如初、无复发之虞、不用继续服药),实则寥寥无几;反之,患病后完全没有任何针对性药物,毫无减缓病情、提高生活质量的医疗康复手段或辅具,这样的疾病也不好找。
也就是说,在“彻底治愈”和“彻底无药”这两个极端之间,存在着一个从“基本治愈”到“减缓病情”的庞大区间,区间里有着大量疾病病种和针对性的药物,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来定义“可治”与“非可治”。即便是同一种病、同一种药,其医疗效果尚且因人而异。同时,医药研发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,每一年,都有许多疾病研发出新的有效药物。判断哪些罕见病是可“治愈”的,哪些罕见病是“不可治”的,须得极其小心谨慎。
甚至可以说,“可治性”的标准,和罕见病目录一样,不界定还好,一旦界定,划入其中的疾病病种自然不复多言,未划入其中的病种,恐怕不少相关病友会有话要说。
但也和罕见病目录一样,怕的不是前进时出错,而是一直停滞不前。哪些属于“可治性罕见病”,我们在地方层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
在此,我们选取专著《可治性罕见病》的上篇,同时也是《上海市主要罕见病名录(年版)》所收录的疾病,即国内相对常见、有明确诊疗方法的56种罕见性疾病(见文末附表1)进行分析,疾病分类情况如下图所示。
从上图可以看出,内分泌与代谢疾病33个,占比50%以上;血液疾病与免疫疾病数量相当,占比14%左右;肾脏、皮肤、五官等疾病极少,分别只收录1个。这些罕见病诊断方式主要是生化方法、基因方法等;治疗方式集中在药物治疗、饮食干预上。
这些疾病发病率相对较高,社会普遍北京一般治疗白癜风多少钱北京中科白殿风医院怎样